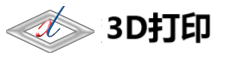一个立方毫米,100纳米精度,成本仅需五六元——这是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教授陈世祈及其团队在纳米3D打印领域创造的不可能数据。
传统纳米3D打印技术虽然精度可达100纳米,但速度极慢、成本高昂。陈世祈团队的技术突破将速度提升1000倍,成本降低95%,一举突破了该领域长期存在的技术瓶颈。
2019年,这项技术在《科学》期刊发表,但陈世祈没有止步于学术成果。工程科研人员的终极目标不是发文章,而是对社会作出贡献,产生真正的影响。陈世祈表示。基于这一理念,在2022年,他与他的博士生一同创立了超奈科技,将实验室技术推向产业化。
陈世祈的纳米3D打印突破源于一个看似简单但极具挑战性的想法:如何将传统的点扫描变成面扫描?
纳米3D打印在学术上被称为双光子聚合或双光子光刻,这项技术早在90年代初就已存在。它就是用一束飞秒激光在光刻胶里面用焦点逐点扫描,速度非常慢,但精度可以到100个纳米。陈世祈解释道。
正是这种“逐点扫描”的工作方式,严重制约了该技术的实际应用。使用传统纳米3D打印技术,若要制作一个尺寸为10毫米、精度达到100纳米的物体,通常需要数周时间,成本高达5万至10万元人民币。因此,这类设备通常只有高校采购——不仅价格昂贵,而且缺乏实用性。
“自2015年起,我们就在思考:如何实现从点扫描到一次完成一条线或一个面的转变,同时保证精度。”陈世祈表示。经过四年的潜心攻关,陈世祈及其团队终于开发出飞秒投影双光子光刻系统,实现了这一技术跨越。
这项技术的应用前景极为广阔。陈世祈介绍,具体应用包括光学衍射器件、定制化的特殊镜片镜头等需要一两百纳米精度的产品。比如说内窥镜远端的一些特殊器件,或者是AR/VR器件里面的元器件等,这些传统工艺无法实现的,我们都可以做。
2022年,依靠这项技术,陈世祈与他从前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Charudatta Datar一同创办了超奈科技,致力于将纳米3D打印机商业化。
目前,超奈科技成功打造出纳米超快3D打印设备样机。该设备横向分辨率达30纳米,速度比现有商业系统快1000倍,打破了分辨率与吞吐量的限制,同时将生产成本降低95%。由此,双光子光刻产品的应用可以拓展到大规模生产和工业之中。
超奈科技在2024年已完成千万级种子轮融资,由科大硅谷子基金领投,合肥种子基金跟投。陈世祈表示,公司正从技术验证阶段迈向规模化生产。
“规模化订单通常需经多轮小批量订单验证。如果小批量订单在良率与精度等指标均达标,那么就可以转化为规模化订单。”陈世祈说。
陈世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者,他的成长轨迹始终与产业实践紧密相连。
1999年在中国台湾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陈世祈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分别于2003年和2007年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和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的选择,为陈世祈打开了产业化应用的大门,也拓宽了他的学术视野。
当时,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MGH)与麻省理工学院(MIT)联合设立了“Translational Research Fellowship”项目,旨在资助工程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出于对光学的浓厚兴趣,陈世祈在获得了MGH-MIT Fellowship之后,加入了哈佛大学威尔曼光医学中心的一个生物光子学团队,致力于将显微镜技术集成到内窥镜中。
在该项目结束之后,2009年,陈世祈加入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平台——由哈佛大学著名化学家George Whitesides教授创立的初创公司Nano Terra。
陈世祈回忆道:“Whitesides教授当时的商业模式颇具创新性,这家公司汇聚众多顶尖人才,为产业中的公司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当这些大公司遇到自身无法攻克的技术难题时,便委托我们这些专家团队进行攻关。问题解决后,双方共同享有知识产权(IP),并共享由此产生的商业利润。”
陈世祈主修机械工程,但在Nano Terra时,由于工作需要,常常需要与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合作。这段经历让陈世祈收获了宝贵的跨学科合作经验。
“我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其实很窄。但在初创公司时,经常要和材料、化学等不同专业的研究员一起探讨解决方案。这个过程让我学会了整合应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因此,到我做教授后,课题组的研究方向就比较广,不受限于本专业了。”
随着初创公司的不断发展,陈世祈的工作重心从技术开发,逐渐转移到管理、募资以及客户管理上。由于自身兴趣更多是在科研领域,因此在2011年,Kaiyun网站陈世祈转投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
作为2011年就来到香港的老港漂,陈世祈见证了香港产学研环境十多年来的显著变化。
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持续强化科创领域投入,2022年公布的《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明确提出,香港须持续完善本地创科生态圈,促进科研成果商品化。
“初到香港时,这里的产学研转化尚未成风气。当时不少人认为教授若凭自己的研究成果创业有严重的利益冲突。”陈世祈回忆道。不过,他并不认可这一说法。他认为,若研究成果始终无法转化落地,最终只会埋没于实验室,这才是公共利益的损失。
随着香港创科生态持续优化,高校对于教授创业的限制逐步放开,且推出众多鼓励政策。
香港特区政府于2023年10月推出“产学研1+”计划,以激励产学研协作,推动“从1到N”的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该计划拨款100亿港元,以配对形式资助不少于100支有潜力成为成功初创企业的研发团队。这些研发团队来自8所受香港特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大学,每个获批项目可获1000万港元至1亿港元不等的资助。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学校开了绿灯,允许教授可以这样做。”陈世祈说,随着观念的转变,大学评价体系也在转变。当前香港高校的评价体系已不再局限于要求教师发表论文,转而将“影响力”——即对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实际影响——纳入新的评价标准。
据了解,RAE是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对香港八大资助大学的评估机制。根据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文件,RAE2026的评估要素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研究成果65%(包括论文、专利等),研究影响力20%(对经济、社会等非学术领域的贡献),以及15%的研究环境。相较于RAE2020,RAE2026将研究影响力的权重从15%提升至20%。
但陈世祈也指出,香港创科生态链仍有一块拼图亟待补上——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原型走向市场产品的过程中,仍存在资金和人才缺口。一方面,产学研转化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需引入具备市场洞察与商业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需要经验丰富的CEO带领初创公司走入正轨。
我们公司严格来说并非传统的师生创业模式,因为我们的CEO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时期的同学,他拥有十余年的管理经验,曾经在不同的初创企业任职。陈世祈说。
对于香港创科未来的发展,陈世祈认为,香港初创企业在将产品推向市场时,更易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对接落地生产。这些城市具备显著的成本优势,而香港的科研能力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制造业优势恰好形成互补。
陈世祈:我成长于中国台湾,本科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之后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机械工程硕士及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波士顿工作四年,随后赴港,至今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
《21世纪》: 在获得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位后,为什么会前往哈佛的医学院呢?
陈世祈: 毕业后,我遇到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与麻省理工学院(MIT)联合设立了“转化研究学者项目”(Translational Research Fellowship)。该两年期项目提供专项研究经费,旨在支持学生将工程技术应用于医学领域。 我博士期间的研究聚焦于微型扫描器件,尤其是内窥式显微镜技术,在光学领域积累了深厚的研究兴趣与基础。若能入选该计划,我便能进入麻省总医院自由的选择课题组进行生物医学相关的研究,进而推动相关技术实现转化与临床应用。Kaiyun网站 最终,我成功入选并参与了该项目。
《21世纪》: 你在博士毕业后加入了当地的初创企业,能否简要谈谈这段经历?
陈世祈: 完成博士后研究后,我加入了哈佛大学乔治·怀特塞兹教授的初创公司。该公司的商业模式并非开发单一产品,而是与多家大型企业合作,专门攻克他们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作为解决方案提供方,我们与合作伙伴共享知识产权并实现商业收益。不过我的背景是机械工程而非化学专业,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与身边的化学家们合作,共同开发技术。
那段经历对我而言,有不小的帮助。进入初创公司后,生存压力迫使我们申请政府的小型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我们直接对接各企业高层,针对他们提出的实际问题,集结团队内机械、化学、材料等多领域专家协同攻关。我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其实相当局限,主要聚焦光学与微机电系统。但经过那段时间的跨学科合作交流之后,当我后来回到香港中文大学从事研究时,我的研究课题就不再局限于单一领域,而是可以与其他专业相结合。
《21世纪》: 从初创企业转向学术界,这似乎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当初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陈世祈: 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希望回到亚洲发展,二是我始终热衷于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推广。当初创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其核心焦点会从技术研发转向运营管理、资金募集和客户维护。若想持续专注于原始创新,学术界能提供更理想的环境。我觉得还是从0到1的过程最为有趣。
虽然回到学术领域,但在初创公司工作的4年时间,让我从公司的视角去看待技术。当我现在回到学术界之后,再向政府申请应用相关的技术时,就会更有说服力。
《21世纪》:你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能否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我们概括一下?
陈世祈:简单来说,我们是专门从事设备研发的团队,主要致力于光机电整合,也就是将光学、自动化和机械等领域进行结合,研发各类设备。我们也会研发显微镜以及3D打印设备。从精密设备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会自主研发移动平台,或者用于医院的快速振动切片机等设备。
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合作模式是:医学院或其他领域的同仁有一些特定需求,但在市面上找不到合适的设备。如果我们评估之后发现,这些设备一方面无法直接购买,另一方面又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技术难度,我们就会为他们专门开发相应的设备。之后,我们会以这个设备为核心申请专利、发表学术论文,而我们的合作方则将这些设备投入实际应用。
《21世纪》: 所以你当前的研究方向更侧重于应用型研究而非基础理论研究?
《21世纪》: 你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期间为何选择再次创办初创企业?这一决策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陈世祈: 作为工程领域的研究者,我们最终的使命并非仅是发表论文,而是创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实际价值。如果我们研发出来的技术没有人能推广到市场的话,我们就应该自己来做这个事。
《21世纪》: 据悉纳米3D打印是你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能否阐述纳米3D打印与传统3D打印的技术差异?
陈世祈: 纳米3D打印在学术领域称为双光子聚合或双光子光刻技术,这项技术并非我们的首创,而是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该技术利用飞秒激光在光刻胶中进行焦点逐点扫描,虽然加工速度较慢,但精度可达100纳米级别。纳米3D打印若要打印一个手持尺寸的物件,通常需要数周时间,成本约5万至10万元人民币。因此,此类设备主要供学术界采购,缺乏商业实用性。
自2015年起,我们团队就开始探索技术革新方案——如何将点扫描模式升级为线扫描或面扫描,同时保持高精度。
2019年,我们成功突破这一技术瓶颈,在《科学》期刊发表了论文。我们将3D纳米打印的加工速度提升3个数量级,同时进一步优化了精度。这项成果已获得专利授权,并成为后续公司成立的技术基础。
相较于传统双光子打印技术,我们的方案可降低约95%的成本。目前每立方毫米的打印成本约为5-6元人民币,而该立方毫米体积内可实现100纳米精度的精密结构。
《21世纪》: 之前跟一些教授进行交流,他们表示许多项目都极具科研前景,但无奈作为教授,在技术推广方面存在困难,导致不少技术可能被搁置长达十余年才有机会转化。
陈世祈: 正因如此,我们才决定自主将技术推向市场。当前,香港的产学研转化环境虽已显著改善,例如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了“产学研1+”计划等专项支持,但从科研成果转化出第一代原型到最终形成商品成品之间,仍存在显著鸿沟。初创企业通常在早期阶段能获取数百万政府资金,或是在规模扩张后获得大额融资,但中间阶段往往面临资金支持的断层。
对此,香港可借鉴美国经验。美国通常通过“小企业创新研究资助”(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Grant, SBIR)来填补从科研成果(论文+原型机)迈向可商业化产品之间的断层。我知道的许多美国的成功企业当初都是依托此类资助逐步完善技术,最终成功实现市场化。
《21世纪》: 你自2011年赴港至今已逾十年,期间香港持续推进产学研转化。从你的切身体会来看,香港产学研氛围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
陈世祈: 我早期到香港的时候,当时并没有产学研转化的概念。但是在最近几年,很明显这个事情受到社会的重视。具体而言,特区政府设立了专项资助计划,支持初创企业发展。重要的是高校态度发生根本转变——允许并鼓励教授参与科技成果转化。长期以来,包括香港在内的许多地区认为教授利用公共科研经费成果创业存在利益冲突。但现实是,若科研人员不参与转化,这些技术往往难以真正落地应用,也就无法创造社会效益。
陈世祈: 初创企业面临的首要挑战在于组建一支成熟稳定的团队。但常见的师生联合创业团队的最大短板在于双方均缺乏实际创业经验。 不过,我们在创办公司时则相对顺利——公司的CEO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拥有逾十年行业经验。在这样经验丰富的掌舵人带领下,企业才能从起步就步入正轨。
《21世纪》: 那你觉得,当前产业界与学术界之间存在哪些主要隔阂?你认为应当如何消除这些隔阂?
陈世祈: 产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的隔阂始终存在,但香港特区政府的创新科技基金(ITF)制度可以拉近双方的距离。针对ITF的项目申请,需要找到企业进行赞助配套。也就是说,你的研发需要获得企业的认可,才能够获得资金、进一步推进。所以如果我们需要申请较大的基金,第一件事情就是结识企业,向他们推销自己的想法,或是了解他们的痛点和难点,这样自然加深了双方的互相了解。
值得关注的是,香港特区政府近年推行的研究评审工作(RAE)也作出重大改革:理工科评估标准越来越关注研究的社会影响力,重点考察专利数量、技术转移成效及初创企业培育等实际产出。这是过去4到5年的一个重要转变。